从阜阳一中出来,沿着人民路往西,穿过东城河,由鼓楼广场继续西行500米,就是西城墙路。沿着西城墙路往南走到底是临泉路,临泉路南边,有个下坡,一条小街,通向阜阳师范大学(当时还叫师范学院)的北门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一中在东城墙的东边,是古城的城外。师范学院在西城墙以内,但位居南城河的南边,也属于城外。从一中到师范学院,是从古城的东门外到南门外,步行要40多分钟。古城面积不算太小。
一中西面不远是东城河,东城河流到南边,叫东清河;西城墙外的西清河流经师范学院,将学院一分为二。东清河和西清河往北都溯源到泉河,泉河往东与颍河汇合后,向东南方向流经颍上,再往东南就通向淮河。这段水路,弯弯曲曲,有100多公里。
有两年时间,我每个工作日的上午都要从一中赶往师范学院,也就是从东清河畔赶到西清河畔。我骑自行车,大概20分钟;骑摩托车,十来分钟。
如果我有一艘船,就可以从东城河往南划,折向西面,进入南城河,沿南城河往西划到底,折向南边的西清河,就到了师范学院。这需要更长的时间,我也没有机会尝试。
清河里行舟,欧阳修干过这样的事。“清河两岸柳鸣蝉,直到焦陂不下船。”当年欧阳修从清河往南直行,不过二三十公里就到了焦陂镇,走水路,一天就到了。
清河原是楚灵王(?-公元前529年)修建的通商渠,后来淤塞,一直到五代时,刺史王祚才将它修复。“州境旧有通商渠,距淮三百,岁久湮塞,祚疏导之,遂通舟楫,郡无水患。”王祚的生卒年不详,他的儿子王溥是北宋两代四朝宰相、史学大家,出生于公元922年,由儿子推知父亲在世岁月,离楚灵王时代过去了至少1400年。又过了大约100年,欧阳修(1007年-1072年)乘船游览清河两岸风光,是托了王祚的福。
这条水道不知持续了多少年,后来还是淤塞了,变成了麦地。不过,如果不直接往南行,而是沿着清河往北行,折向泉河、颍河,最后到淮河,大约要7天时间。今天还可以行舟。可是,没听说有谁走过这样的水路。我也只是想一想,上哪去找这样的船呢,还要有航运证、驾驶证。
如果晓行夜宿,在麦地旁边,沿着这样的河流航行,应该是一件有趣的事。我站在师范学院的清河桥上,看着一弯浅浅河水,想,城外的河水一定不是这样,坡度低缓的河床上面是无边的麦地,麦地上散落着几百个村庄。河道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南,有时还折向北边,拐一个弯又回到南边,千回百转,柔软和缓地铺展在大地之上。
如果我乘舟水上,晚上也可以随时停泊上岸,睡在麦地里,樱桃树下,沟坎之间。黄淮平原,一马平川,月亮均匀地照着麦子,连阴影都不会有。不像皖南的秋浦河,两岸是高山巉岩,林木幽深,神出鬼没。别说晚上,即使白天开车在里面也是半天看不见一个人。我在秋浦河里航行,晚上绝对不敢随便上岸,谁知会遇到什么。
而在这边,颍河两岸要么是豆子、玉米,要么是红芋、小麦,无边无际的庄稼,俭朴的农舍,还有牛圈,连环绕村边的树林也是稀疏的。一切都袒露在大地之上,一切都被日光月光照彻。我晚上就睡在麦地边缘,不要任何遮挡,四仰八叉,让月光将自己穿透,变成一个淡黄色的、透明的人,和这些麦子、泥土一样。
颍河两岸深厚的沙土,充沛的阳光,适合生长樱桃,这是江南少见的果树。在麦地和村庄之间,有时还有这样的樱桃林,让人停舟系缆。清晨的阳光穿过樱桃叶,将绿色的叶片照成了淡淡的金黄色,叶片呵护的红樱桃晶莹剔透。如果睡在樱桃树下,睁眼就能看到一颗颗红色的梦。
当然,也可以睡在船上。河床不是很宽,没有大风,都不用抛锚系缆,一只小船能漂到哪里呢?醒来时霞光万丈,两岸是看不到边际的红芋、麦子。
就这样,从袁寨、老庄、张楼、沈庄、饶庄、后庙、祁庄、汤庄、黄台、八里河、陡岗,一直到冯家行、八里垛,河道直接向东,由神路口、沫河口,冲向胡台子,就进了淮河。
村庄附近有莲藕,塘里有鲤鱼,8月会酿新酒。有穿着光鲜的女孩子和男孩子,在村道上奔跑。王祚和欧阳修当年看到的景物,今天还在。今天有更宽广的高速公路,还有高铁,很少有人会乘船经过这些古老的河道了。
当地文化人说,清河就是灵渠,他们说起灵渠和楚文化的关系,头头是道,我听了却一片茫然。我经过清河的时候,总想找到一艘小船,往北,往东,重复一次缓慢的行旅。
江南的诗句里飘满了酒旗,“风吹柳花满店香,吴姬压酒唤客尝”;颍河两岸也有柳树,也有酒家、渔翁,“焦陂荷花照水光,未到十里闻花香”。这里的荷花泼天生长,连花瓣上的红晕都是奔放的,实笃笃的,不像吴姬那样娇羞。
我喜欢这样的河流。有朝一日,我攒够了钱,一定买舟东下,在麦地簇拥的颍河上,开始一次期盼多年的航行。
(作者系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,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高中语文教研员,1995年-2001年间在阜阳一中任教)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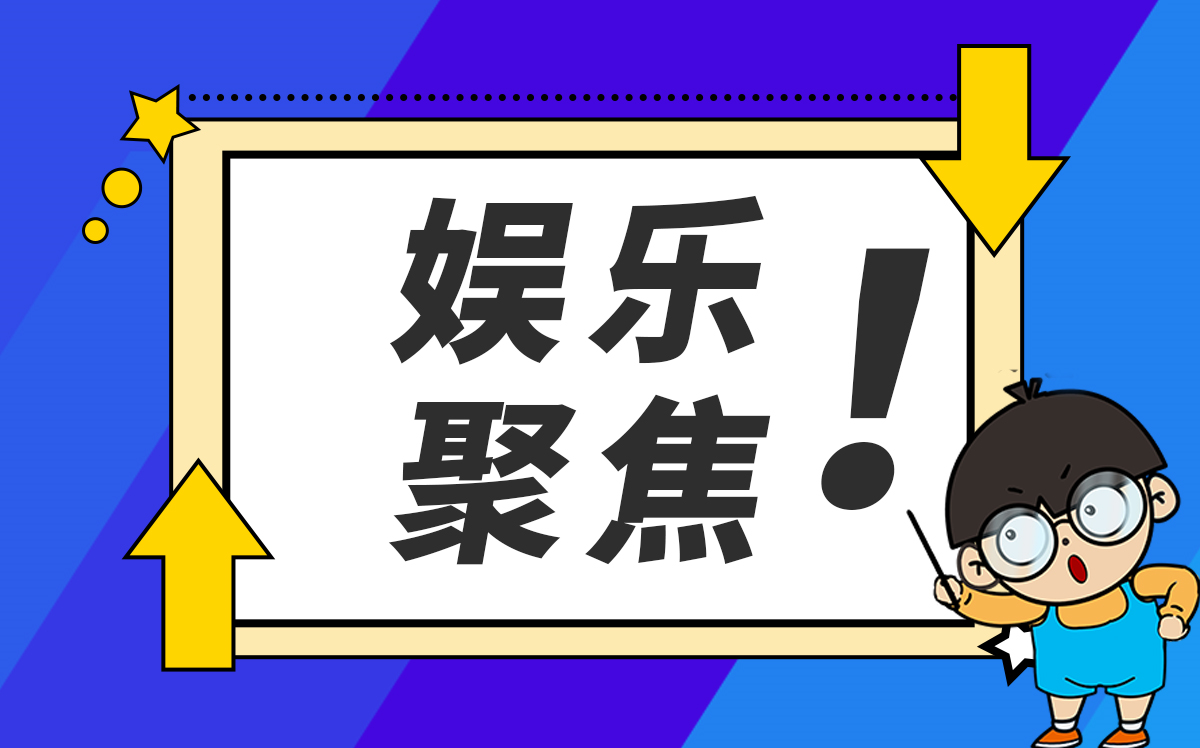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